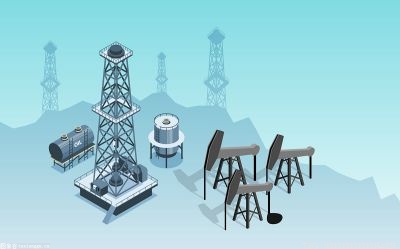仙侠(注意:本文纯属虚构)
第五十二回 齿轮
却说剑圣离去,王怀玉与李褐眼前一黑。端木遥见徒弟渐睁眼,连忙呼唤几声。铁河则去李褐身边蹲下静候。王怀玉茫然道:“师父。”端木遥收回剑指,笑道:“哎。”此时,李褐也苏醒过来,伸个懒腰,惬意地吁口气,又起身走至王怀玉身边,笑着凝视她。王怀玉瞧见那小子的傻样,现些喜色,拱手对师父说道:“徒儿鲁莽,叫师父牵挂。”说着,要叩首。端木遥扶住徒弟两臂,说道:“没事就好。就是我儿子、儿媳妇操劳了。”王怀玉站好,面向铁河,作揖道:“多谢师弟。”刚弯腰,被齐玲把住。齐玲嗔笑道:“姐姐不谢我,妹妹生气了。哼。”王怀玉两手握住妹妹双手,笑道:“妹妹说的什么话,姐姐谢你还来不及呢。”齐玲笑道:“姐姐好就是妹妹好。”铁河别过头,说道:“你俩洞房去吧,看不下去哩。”众人为之一哂。齐玲就给王怀玉介绍吴萱。王怀玉见了狐仙,自是高兴,又向陆五味等人致谢。端木遥一直盯着李褐,眼皮都不眨。李褐发觉目光,挠挠头,望向别处。铁河就走到端木遥身边,附耳低语。端木遥听了,说道:“嘴巴这么多,退开。”铁河笑了笑,说道:“师娘早做打算,此乃天作之合。”端木遥寻思:“给别人听了,好像给我说媒。”不理会。
楚玄捋一捋胡须,命道:“将那饕餮绑缚好,带回定安。”几名甲士立即尊令,取来手腕粗的绳子,把饕餮四足束牢,再用禁法旗包住扎了,穿根棍子抬着了,还把先前竖立旗帜收了。楚玄对众人说道:“此事已结,我先回府复命。” 众人拱手相送,楚玄回礼,领军士下山。这时,一道黑影从林子里掠过,直冲饕餮。铁河看得清楚,正是饕餮魂魄,便拔刀直刺。魂魄后跳躲开,张口猛吸气,四周积雪尽入其腹,瞬间膨胀为一个十丈高的庞然大物。铁河对楚玄说道:“员外且去,这里有我等对付,万无一失。”楚玄略一思索,说道:“千万小心。”又催促军士加快脚步,跑在队伍后头。齐玲早用出真炁人形。那人形有百丈高,右掌按下,却穿过饕餮魂魄。她就拔出解牛剑,跃至敌人面前,使劲一劈。那人形动作同样,只是握着透明真炁聚成的巨剑。魂魄害怕解牛剑,不敢硬接,望边上一蹿,躲过了。齐玲道:“有些本事。”音落,立于地面,双手反握剑柄,插入土里,闭目控制真炁人形。魂魄一连躲开十余下攻击,忽从人形胯下钻过,直扑齐玲。铁河早赶到,使出掌心雷。魂魄身形一折,又冲向李褐。王怀玉掣出东来剑,刺出,粉色真炁如箭,瞬息而至。魂魄头部出现个大洞,势头不减。李褐当即蹲下,抬头见魂魄飞过,又撞向陆五味。五味知味,两腿前后跨着,使出金光罩,硬抗下,向后滑行丈余。卫辰通大吼道:“雷公助我!”以剑接天雷,转身一甩,击中敌人。那魂魄登时散去,又成团,飞向林中。铁河叫道:“我来!”声尚在,已化为道金雷,穿过魂魄。刀入鞘,敌消亡,凉风卷过,叶缤纷。端木遥欣慰地笑道:“后生可畏。”陆五味见铁河走来,说道:“我们忙了半天,风头都给你出了。”铁河拱手道:“这是各位抬举啊。”陆五味笑道:“老弟,这你得请大家喝酒。”铁河道:“好,一起喝酒去!”大手一挥,带头下山。端木遥叫住王怀玉,问道:“你和那小子什么关系?”王怀玉粉面含羞,低声道:“朋友。”端木遥笑道:“我可听铁河说了,你和他是很好的朋友。”王怀玉“哎呀”一回,抱怨道:“这个妹夫。”端木遥道:“李褐是吧,我见他倾慕于你,可别一时冲动,那样不好,懂?”王怀玉道:“我骗他,骗他……”端木遥道:“说嘛,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?”王怀玉咬着牙齿,缓缓说道:“我骗他我有心上人了。”端木遥笑了几声,说道:“还是年轻人会玩。呵呵,你自己把握。”这老妪笑得合不拢嘴,又问:“剑谱在哪?”王怀玉道:“师父稍候。”赶上队伍,唤来李褐,一同去屋子拿了剑谱,再拓印了元神出窍之术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林子里安静下来,一缕黑气飘出草丛,飞往天边。
正是酷暑时分,众人入得酒肆,于二楼临河包间内坐定,偶有凉风穿堂而过,倒也不热。王怀玉笑道:“今个我东来门请客,各位随意,酒肉撒开肚皮吃。”齐玲笑道:“本该是我夫君请的,却叫师娘破费。”陆五味捋了龙须,笑道:“哎呀,我与老弟相识以来,还从未喝过他的酒,真个小气。”其余人笑了。铁河笑道:“一直没机会么,明明是你怜惜自家钱财,盼我还礼。”陆五味道:“快了,快送礼了。”铁河道:“还有多久,我也好准备。”陆五味道:“我正筹划,等我喜帖便可。到时都来。”众人自是答应。铁河笑道:“大哥神速,半年就成了。”陆五味道:“这是我雄姿勃勃,一举拿下。”那三个娘子听了,都羞红了脸,就去阳台上坐了,说些女儿家的话。铁河见状,笑道:“好不知羞,没得面皮。”高木笑道:“陆师弟这人得意了就飘,口无遮拦。”卫辰通道:“真不知道陆娘子怎看上你的。”李褐初来乍到,只与铁河熟悉,微笑着不多言。不多久,酒菜上来,热菜还需一会。王怀玉叫酒保另搬一桌,要食物同样。男子那桌喝了一道,陆五味问李褐:“李师弟可否告知师承,我等也好择日拜谒。”李褐道:“师父不让说,恕我无礼。”说罢,自斟一杯敬过饮下。铁河道:“约莫是哪位世外高人,不愿留虚名。”陆五味道:“既是如此,那就罢了,喝酒。”随即拿起酒壶,筛与各位。高木道:“我去看看。”之后起身,来到吴萱身边,携她走到一旁,小声吩咐道:“酒少喝,不要醉了。”吴萱略鼓腮,说道:“我知道。”高木道:“知道就好。”笑了笑,回了位置。待吴萱落座,齐玲关上门,将两个门环用绳子绑牢,坐定笑道:“他还管你喝酒?理都不用理。”吴萱道:“木哥哥对我好,我自听他的。”王怀玉笑了。齐玲喝尽碗中酒,脸蛋和手渐浮红晕。她给自个倒满,问道:“高师兄欺负你没有?”吴萱摇摇头,说道:“没有。”齐玲又问:“你俩已成婚了么?也不叫我等过去热闹热闹。”吴萱道:“已,已洞房了。木哥哥说,一切从简。不过,结婚那天好酒好肉,我吃了个饱。”齐玲笑道:“哈哈,诶,神仙眷侣。”又道:“以后高师兄欺负你,你就找我,找王大姐也行。”吴萱抿了嘴,点了点头。王怀玉道:“我也不老啊,总是叫我大姐。”呷口酒,夹来肉上香菜尝了。齐玲夹个鸡腿到吴萱碗里,劝吃,又对王怀玉说道:“大我三岁吧,就是我大姐。况且那傻小子更该这样唤你。”王怀玉道:“你才傻。我家阿褐可不傻。”齐玲笑道:“哟,才多久,就是我家你家的了。大姐不知羞。”王怀玉笑着瞪了对方一眼,说道:“反正亲过了,他要跑我还不让哩。”吃片卤猪头肉,啜了酒。齐玲问道:“谁先的?”王怀玉借着酒劲,说道:“我呗。他还以为我有伴侣,哎哟,可伤心哩,哇哇哭。总觉得我和他是做坏事。”吴萱啃着鸡腿,说道:“大姐这样不好。”齐玲道:“狐仙说的对。大姐跟他要讲清楚么。”吴萱道:“别叫我狐仙,我年纪小,叫妹妹就行。”另两个娘子笑了。王怀玉道:“怎么说清?就他那傻样,我就不讲。”齐玲道:“对啊,多刺激。大姐会玩。”王怀玉推了齐玲肩膀,笑骂道:“去你的。”齐玲摇头一叹,说道:“可怜李师弟,被哄得团团转。”吴萱道:“大姐不要这样,俩个人之间,最重要的是坦诚。”齐玲笑道:“对,坦诚相见,才能甜如蜜糖呐。”王怀玉别头憋笑。吴萱刚颔首称是,随即反应过来,对齐玲说道:“不理你,长舌妇。”之后,这仨娘子又聊起悄悄话。男子喝酒向来喜欢吹牛,且米酒好入口,后劲迟迟来,更助情趣。他们几个酒酣脸流汗,就全脱了上衣,打了赤膊。喝了阵,陆五味摸摸湿漉漉的胸膛,觑着眼睛说道:“关的甚么门,热呀!老弟,你去开来。”铁河拿壶倒酒,却倾在桌上。他道:“我不去,高师兄去。”高木打着盹,抬首道:“小卫去。”卫辰通抱着酒坛子,喃喃道:“美女,啊美女。”说着,憨笑起来。这下激起阵笑声。李褐道:“我来。”晃晃悠悠站起身,扭至门口,一下倒在门板上,倚牢,右手摸到闩座,拉开些,却见一根麻绳。他唤道:“开门呐。”王怀玉转头一看,过去解了绳子,再进屋来,赶紧扶住李褐,说道:“都醉了。”齐玲看了天色,只见晚霞遍布,灿灿然,忽凉风拂面,又瞧河上船只已稀,屋上炊烟尽斜。她说道:“我去租来客房。这些男子且扔在这。”音落,下楼去寻店家。王怀玉哪舍得将李褐扔了,把他放下坐好,盯着对方脸庞发着呆。李褐道:“大姐,你怎么有好多眼睛啊,完了,我醉了。”说完话,呜呜地哭。王怀玉悲上心头,抚着李褐胸膛,安慰道:“不哭、不哭,没事的,不哭。”陆五味道:“啊,这才凉快。你哭个什么?你大姐心里没有别人的。”吴萱也进屋了,见高木趴在地上打鼾,就将他翻过来。李褐哭道:“是我不对,是我害大姐做坏事了。”卫辰通仍抱着酒坛子,含混不清地说道:“做了就做了呗,天塌了卵子顶着。屁大点事。”又念叨起心中美女。铁河两肘搭桌,撑着身子,大着舌头说道:“对,话粗了些,在理。”王怀玉闭紧嘴巴,不理会这几个醉汉。
天色已暗,远处,星汉从丹穴山之巅斜弯出来,白闪闪。齐玲上楼说道:“商旅颇多,只余两间客房。”王怀玉道:“分开来呗。”三位娘子就先把自家郎君扶回房里,再去理会陆五味与卫辰通。卫辰通听得齐玲呼唤,睁眼见那三人,说道:“哦,三个美女伺候我,真好。”挨了顿掐,哀嚎不止。只见卫辰通左齐玲,右怀玉,前面带路是吴萱。他刚进屋,就被三位娘子扔在地上。王怀玉看着面前五条赤膊大汉,问道:“妹妹,谁来照顾?”齐玲道:“照顾什么?没吐就行,我们仨回屋歇息。”吴萱道:“齐姐姐,这样不好吧。”齐玲道:“无妨,还没烂醉。要吐绝对先醒。”便牵起姐妹的手,拿了衣裳去澡堂沐浴。夜里,这姐妹三个同床共枕,盖一条毯子。齐玲个大,躺在中间,左搂王怀玉,右抱吴萱。她打趣道:“啊,天下谁有我这福气,真个得劲。”王怀玉笑道:“不管他们真没事么。”齐玲道:“他们,我看你是想着何时才能跟李师弟洞房吧。”王怀玉道:“去,净说瞎话。”吴萱伸手遮住口鼻,笑嘻嘻的。齐玲道:“天色不早,睡觉吧。”闭上眼睛。王怀玉道:“是困了,歇息、歇息。”吴萱道:“嗯。齐姐姐好软,真舒服。”脸枕对方胸脯,侧卧着睡了。
次日,众人欲归家,王怀玉于酒肆铺下酒席践行。几个男子之间倒是干脆,说几句祝福话语便罢。三个娘子却执手相看,泪串珠,难以分舍。她们各自郎君劝了会,才愿启程。
话分两头。那一缕黑气直追楚玄而去,于定安见饕餮肉体焚化,便寻宿主。圣人与贵妃住在兴庆宫。黑气本想附身,却被宫外贴着的门神挡下,差点消散,又欲在大明宫宣政殿行事,远见圣人天命紫气及文武两班朝臣浩然正气,更不敢入。于是,黑气只能徘徊游荡,终无力飞动,待在殿顶瓦上等死。这日,殿外走来一人,紫袍金鱼袋,腹垂过膝,待他进殿,才看得是金玉腰带。黑气见此人皇城外随行扈从仪仗千人,秉有旌节,朝会列武将之首,且貌似忠诚却敛反意,甚合。夜间寻其暂住驿馆,入耳目,以壮滔天贪欲,成饕餮“美名”。明日,此人去往城东华清宫面圣。先拜贵妃,叩首唤道:“儿子拜见娘亲。”贵妃收个年纪这么大的干儿子也不害臊,应道:“哎——乖录儿。”引得宫女太监一阵笑。圣人笑道:“果真是个孝顺儿。”录山这才拜圣人,唤道:“儿子拜见父亲。”圣人道:“好……起来吧。赐座。”太监搬来一个床榻,安录山半跪着起来,挪到榻边坐下,床板“嘎吱”一响,吓得站直。贵妃遮嘴大笑,身不歪,体不斜,头亦不仰,甚是端庄。圣人拿起金杯喝口酒,笑道:“娘子,又是你做的。”贵妃笑道:“三郎,你瞧录儿那样,真个好笑。”安录山挠挠头,又坐下去,发出声响来,只得再起,说道:“娘亲特意要儿子出丑,儿子伤心了。”贵妃笑意不减,说道:“你伤得什么心?整日里胡闹,折子都到三郎这里了。”圣人道:“我是不信,儿子心迹,我还是看在眼里的。”他招了手,随侍太监从屏风后端来个木托盘,上有奏折。圣人道:“你看看,尚书是否句句属实。”挥了手,令贵妃退下。安录山看了会,跪地哭道:“臣不识字。是陛下越级擢升臣,遭那姓杨的忌妒,才要杀臣。臣冤枉,臣侍陛下如父,唯有一片忠心。”话罢,涕泗横流,掩面痛哭。圣人面有悲意,上前扶起安禄山,说道:“我儿受苦。”安禄山哭得更大声,叉手道:“陛下……”圣人道:“将眼泪擦干。来人,把床榻换了。”太监立即搬走坏榻,运来个好的。圣人道:“唉,差点误杀忠臣。”拍拍安录山肩膀,说道:“我升你为左仆射。”安录山道:“臣惶恐。臣一介武夫,不知政事。望陛下收回敕命。”纳头便拜。圣人负手道:“我给你,你就拿着。与我守好边关便可。”安录山再拜道:“臣领敕。”圣人现出笑意,入了座,说道:“我家娘子呢,娘子,出来吧。”贵妃出得屏风,一脸娇笑,端着一金壶酒。她坐在圣人身边,斟了一杯,又端起杯子奉上,笑道:“三郎你瞧,这酒颜色多艳。”圣人笑着接过酒杯,笑道:“哪有娘子艳。”饮下一口,赞道:“不错。”再道:“我儿坐呀,赐酒。”宫女随即端来案几,摆上果品美酒。另有一出众宫伎跪着伺候。之后进来一队宫娥,随曲舞蹈。圣人酒酣,命安录山跳胡旋舞,自个也搂着贵妃穿行于舞队之中。只见安录山拿起金壶,旋转着走向圣人,酒满而不撒。他单膝跪地,朝贵妃说道:“娘亲喝酒。”贵妃单手托着金杯去接。安录山双手拿壶,斟满。贵妃饮一口,又拿在圣人面前,娇声道:“三郎喝一口。”圣人收敛动作,笑道:“娘子疼我。”尽饮下。贵妃道:“这是儿子孝顺。”圣人见安录山单腿跪着,说道:“我儿跪着做什么,跳啊!”安录山道:“好哩。”再给贵妃倒酒,旋转着来到圣人座前,放下酒壶,再绕着场地边转边拍手,真个灵活。
入夜,宴会散,圣人醒转来,洗把脸,独自进入书房。门口自有千牛卫把守。他点起油灯,观看墙上地图,想道:“安录山时日无多,我虽老迈,定耗不过我。若真反,只需守住关隘,百万之师又如何,且,我陇右精锐一到,围左右,断后路,剿灭之易如反掌。”他拿起笔,在地图城池上画了一竖。一竖为一万士卒,已有二十竖。圣人不言,继续想道:“已有十五万精锐,又募了五万人马训练。唉,望你思及皇恩,别受门阀蛊惑,悬崖勒马最好。不稳妥,明天见一见那几个族长,安抚一番,多送些礼物,加爵位官职,该有些效果。还是隔几天见,免得猜忌。阳奉阴违怎办?真个有狼子野心……不,他们不敢,我是君,他们是臣,定不敢效仿前朝,真敢,那就是异族南下,这些个门阀仍出不了头。清君侧么,呵呵,大略是这样了。诶,到时娘子有危,没了多可惜。不可能,那帮人哪有这么大的胆子,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作诗赋曲不好么。”圣人吹灭油灯放了,出门来。一个太监提着灯笼走到他身边,弯腰照路。这般,圣人才去找贵妃消遣。半夜,驿馆,安录山睡在床上,手脚蹦几回,忽然坐直,瞠目喘息。先前陪酒宫伎醒来,问道:“节帅怎么了?”安录山满头大汗,说道:“我做了个噩梦,十分吓人。”宫伎笑了,乘月色寻到手帕捏着,给他擦脸,说道:“节帅常年征战厮杀,英雄男儿,怎被个噩梦吓到。”安录山道:“我梦见一个人脸怪物啃食我腹。”宫伎皱眉,又给他擦身子,说道:“还真是吓人。我听人说,噩梦不过是白日里太紧张所致,好好歇息就行。”安录山怔了会,松口气,说道:“是呀。”他搂来宫伎,单手掐住她脖子,笑道:“你这个小娘子倒是体贴。”宫伎一脸可怜样,目含春光。安录山道:“这宫里的就是不一样。说,你想要什么奖赏?”宫伎噘嘴说道:“奴也不想要什么,只愿陪在节帅身边,日夜侍奉。”安录山道:“多你一个不多。见你解人意,明日我便向陛下要你来。”宫伎抽泣一声,抱住对方脖子,哭道:“节帅于我恩如再造,以后,奴定殷勤伺候,做床当垫。”安录山心情好转,自不去想那噩梦。
言归正传。铁河与齐玲告别好友,归山生活。山高入云,气温低些,就是夜里蚊虫多。齐玲在圩上买了个蚊帐,一些蚊香,本要等铁河做织机,想着钱有富足,便买了个新的。每日里寅时起床练功,吃过早点开始纺布,至半夜才歇。铁河则扛着幡子,卖些膏药换钱,因价格便宜,生意极好,却没几天给人打了。饶是他会仙术,也得按江湖规矩行事。这天夜里,齐玲看着丈夫身上淤青,揉揉眼,说道:“我去打回来。”就要出去。铁河笑道:“无妨,小事而已。”齐玲停在洞口,说道:“给人白打了。”铁河道:“玲儿你坐过来。”齐玲就坐在丈夫身边。俩人共坐一床。铁河说道:“我这是没给人情,才遭此难。我是不想给,师父都不给,我也不给。”齐玲道:“你也不知道还手。”说着,撇了嘴,两手握住对方大手。铁河道:“习武之人,不可妄动。那帮人一麻袋罩下来,不好用法术,且用的棍子,用兵我就跑。嘿嘿。”齐玲忍不住笑了一下,嗔道:“瞧你这憨样。我拿热汤来给你敷一敷。”铁河道:“不用,不疼。我想以后做什么。”齐玲道:“你人情不送,做什么都挨鸟。”铁河笑道:“粗俗。”顿了下,又道:“不过在理。”齐玲想起乌鸦妖送的糯米酒,当即舀了两碗,分给铁河,说道:“干。”铁河笑了笑,碰一下。俩人一饮而尽。齐玲觑眼皱眉,手背遮嘴,半天哈出一口气,说道:“我嘞乖乖,莫不是掺了白酒,真得劲。”铁河道:“没想到这乌鸦妖是个酒虫。”齐玲收碗去洗,说道:“总是叫人乌鸦妖也不好。”铁河道:“是啊。明天买些礼物与他,你说送什么好。”齐玲收了碗,坐回丈夫身边,略思索一会,说道:“买些干货,差不太多,这样好。”铁河道:“嗯,鸦兄肯定喜欢。”齐玲捂嘴打个哈欠,说道:“天色不早,歇息吧。”然后到外头厨房点了一根艾香,把炭用灰盖了,又进去山洞闩了门,插在个炉子里,吹灭油灯。铁河躺在石床上,叹道:“我明天去河边看看。”齐玲道:“好呀。你脱衣裳呀。”铁河道:“你来。”齐玲笑出几声,说道:“懒。”给他宽衣。
次日,铁河出门下山,大步来到河边码头。这里距南阳山约百里,平时运些茶叶、茶油、草药、生姜等小宗货物。铁河很快找到管事的,搬运起货物来。酬薪日结,给的不少,多是健壮年轻人。中午,菜是猪油炒的,有点肉末,饭无限。小郎君笑了,哐当当干掉十大碗。管事的见铁河来打饭,笑道:“小子个大,饭量也大。”铁河笑道:“这里伙食好。”托碗伸手,傻笑几回。大娘给他打满米饭,笑道:“别给阿郎吃穷喽。”管事的说道:“这小子有把子力气,吃,使劲吃,管够。”铁河端着碗回到同事那里,蹲在地上,夹了些肉末茄子至饭上,飞快吃光。旁边同事说道:“阿铁,你也吃点菜呀。”铁河笑道:“我够了,啊,喝点水来。”说着,去水缸边舀水入碗,用筷子将米粒拨下,全喝尽。同事们见这小郎君懂事,不由得欢喜他。下午,铁河扛着五袋大蒜,行至船上,忽闻歌声。他放下货物,远眺去,见河上一小舟,立俩人,一客,一船夫。船夫摇橹,客歌唱。偶尔听得:“‘会当临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’”铁河寻思:“玲儿说,慢悠悠是雅乐,急匆匆是俗乐。可这曲子俗,诗却极好,怪哉。”想罢,下船干活。夜里回到山洞,铁河将诗句讲了。齐玲道:“嗬,杜子美!”铁河问道:“肚子美?”齐玲道:“你肚子才美。杜甫,字是子美。”见铁河求知眼神,接着说道:“我在定安时听过唱过,诗极好。有一次,我在楼上见他跟在个贵公子后头,唉。”铁河道:“如此诗思,应该是书香门第之后,怎没傲骨?”齐玲问道:“你有傲骨?”铁河笑道:“我本布衣,要这做甚?不过,能写出这种诗句,不像那种趋炎附势之徒。”齐玲道:“他还写诗嘲讽过自己,叫什么?对了,这句,‘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’却给那些纨绔唱去,无病呻吟,令人作呕。”铁河道:“他唱他的,你恶心干嘛?”齐玲笑了一下,说道:“对。可前面是‘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’我唱给你听。”她抱来琵琶,说道:“用雅乐。”随即拨弦歌唱起来。铁河就煮了一壶刚买的红茶,与妻共饮。
虎贲
上一篇:五巨头联合组建RISC-V芯片公司,目标:汽车、手机、物联网
下一篇:最后一页
X 关闭
Copyright © 2015-2022 北极科技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:浙ICP备2022016517号-19 联系邮箱:514 676 113@qq.com